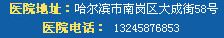黄河原创文学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wwjm.com/zcmbjc/11179.html
文学公众平台
黄河文学原创频道
作者简介
白默,山西省垣曲县新城镇人,山西省稷山师范毕业,年6月——年3月在皋落初中任教,喜好文学,有部分作品见于网络。
初秋时节,连降骤雨。三年前,父母的葬礼上,也是这样的雨,疾如万矢乱飞,势如天河倒悬。阴阳交替,季节轮回,父母却一去再不复返。静夜无眠,思念如烟。昨天,过完父母的三周年。父母辛苦一生,白头偕老,虽够不上传奇,足称得上典范。三年前,父母脚跟脚离开我们,相隔只有一天。父母如天,恩深似海。一个离去,已似剜肉戳心,三天双亡,情何以堪!送走父母,很长一段时间,胸口隐隐作痛。医院就诊,均不明所以。后来时间一长竟自好了。现在回想,应是当时悲伤过度所致。父母携手七十多年,从初涉世事到为人父母,从含辛茹苦到儿孙满堂,从家里家外到一村老小,可谓是结于蓬蒿,起于乡野,兴于桑梓,终于老泉。父母白手起家,是同时代大部分家庭的缩影,是新中国新农民一生的样板。七十年前,母亲嫁到我家。记得好像听母亲说过当时是由一位远房亲戚看着俩娃都没爹没妈,实在可怜,聚到一块过活,互相有个照应,才走到了一起。母亲的娘家是现在新城的刘张村,家里原有三间北房。父亲三岁沦为孤儿,虽然爷爷在时家道殷实,但爷爷去后,田业无剩,母亲来到我家时只有一眼土窑几间偏屋赖以栖身。但母亲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她的北房走进了父亲的土窑。来我家时,母亲还有一个孤儿侄女,无依无靠,母亲不忍丢下,便一起带了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大姐。也许是天意,父母走后不到一个月,大姐也病入膏肓,相跟而去。这个家庭最初的三个人又以神话般的结局在另一个世界相逢。父母一生养育了五子五女,我是老小,俗称窝底。因我唯一的姨妈只有表哥一个独子,母亲便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我们的亲大姐(排行二姐)过给姨妈做养女。姨妈家在毛家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小时候跑亲戚,二姐家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二姐和姐夫为人宽厚,颇有人缘。虽然也是家常饭菜,但我们一到那里,都想多呆几天。后来,二姐一家又迁回我们村。为回与不回的问题,我们开了几次讨论会,姊妹们都主张二姐回来。但二姐回来了。我却离开了村子,成了一个游子。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一起相聚。母亲带来一个姐姐,送养一个姐姐。都是困难所迫,万不得已。小时候常听母亲念叨二姐的小名,说娃那么小,还去地里干活,咋能干动?说着说着禁不住就流下泪来。母亲一生都在劳动。不是在家里,就是在地里。劳碌辛苦,持家有方。母亲矮小的身躯里蕴藏着永远使不完的劲。包产到户后,生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身上穿的碗里吃的,一年一个新起色。每年过年,母亲总要给父亲置新衣,也给我们做。母亲的手很巧。每次穿上新衣服出门,村里的婆姆婶嫂都会夸母亲的手艺好,我们听了,心里就像喝了蜜。但母亲永远穿的是一身旧衣,几十年如一日。整洁朴素。还有补丁。补丁上时常沾着洁白的面粉,各色的线头。那是母亲留给我的最美的形象,明星天使圣母与母亲比起来,也是母亲光芒万丈。父母节衣缩食,最大的愿望是儿女们有个好前途。但在那个时代,想要出人头地,只能靠自己奋斗。父母尽己所能,为儿女们找寻出路。我的四个哥哥,有送到三线的,有送到部队的,有送去学木工的;几个姐姐,两个供到了高中,一个送去学医。我是上的师范,现在是一名正科级党员干部,从事移民工作。姊妹们虽不富贵,但都自食其力,日月兴旺。勤劳,成就了母亲也摧残了母亲。母亲晚年,患上了高血压。每次回去,我们都建议她和父亲去我们家住。父母总是以在家惯了为由婉拒,独立生活。即使偶尔进城,吃了晌午饭,便开始催促送他们回去。只有那个花果芬芳、葡萄满藤,石榴飘香,鸡跑狗叫,炊烟袅袅的篱笆小院,才是他们的乐土。而我们的乐土,永远是父母所在的地方。母亲八十大寿以后,我们商议,以后,父母过寿,由我们兄弟四人轮流做东,不能再让父母忙前忙后了。但母亲不肯闲着,过寿前一天,非得亲手蒸几锅馒头,说是买的馒头不好吃,还说我们走的时候不能让空着手回去。大约两千年的时候,给母亲过完生日回来,半夜零时左右,三哥打电话来说母亲不行了,让赶紧回去。我一听,头脑都空了。一路加油狂奔,泪飞如雨。一定要在有生之年见母亲最后一面。回去时,刚进院门,我就大喊“妈”冲进内屋,只见母亲牙关紧咬,脚乱扑腾,我万箭穿心,抱住母亲又摇又喊,但母亲双眼无神,好像不认识我一样。姊妹们手医院,检查后诊断是脑出血,病因是劳累过度。住院半个月,母亲康复出院,恢复如常。我们都说母亲福大命大,老天保佑。但第二年,同样过寿,同样做事,同样犯病。这次出院,我们商量,必须轮流侍候,不敢让父母独自生活了。充分尊重父母意思,愿去谁家谁接走,愿意在家回来管。从此,父母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一日不如一日。到了最后,母亲小脑萎缩,完全丧失生活能力。不能咀嚼,不认识人,两便失禁,成了名副其实的植物人。只能吃点流食。瘦的皮包骨头。原来一百三四十斤的身体最后剩下大概五六十斤,让人一见泪目。但父亲身体尚可。姊妹们在一起时免不了商量父母后事。都觉得母亲身体不好,应早做准备。后来置办时,考虑父亲年纪也大了,干脆一起置了。但好像母亲一直是渐进式的走向人生的终点,而父亲却加速奔向生命的尽头。起初是饭量锐减,后来是举著困难,需要像母亲那般喂食。记忆力也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降,三五天之内吃喝拉撒全都失能。但父亲临终前夕却十分的清醒。父母临终前在我家度过。那天晚上,我侍奉父母吃完晚餐。父亲坐在床头,我坐在他身边,给他点燃一支烟,帮他夹在手指间。他只抽了一口,便甩在地板上,说“不吃了,苦”。他主动讲起他的父亲母亲,我的从未见面的爷爷奶奶,也许是分离太早,也许是临终交代,没有悲伤,没有激动,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我哪里知道那是父亲和我的生死之谈?我只记住了我的爷爷有兄弟四个,爷爷叫思明,排行老二,四爷叫思聪,中途夭亡,大爷叫思温,三爷叫思什么,一时想不起来了。直到刚才忽然想起古代好像有一篇文章,里面有“视思明,听思聪——”,百度一查,孔子的《论语季氏》有“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懿”,应该是思懿。因为小时候每年过年换牌位,都是我写父亲贴,记得这个字很难写。从这四个名字里,我感觉到太爷一定是一位饱学之士。后来见父亲显得疲乏,便将他扶好躺下,用薄被单苫住睡了。平时我一睡下,半夜是不起来的,但那夜躺下不久却奇怪地憋醒。上完卫生间,返回卧室时,发现父亲一条腿耷拉在地上,赶忙进去把父亲的腿扶好,又发现上半身凌空欲起,姿势惊悚。我又把父亲身体放平。欲转身时,突然莫名其妙一个激灵。近身用手背在父亲鼻子上一试,不妙,再试,父亲已断气了---我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看到过亲人生离死别,却从来没有设想过我和亲人的诀别场面。那一刻,我和父亲近在咫尺,却阴阳两界,触摸着父亲余温尚存的身体,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生离死别----就是让你此生再也听不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喊你乳名,再也吃不上柴火锅头的家常饭菜,再也没有老院里姊妹们热闹的欢聚,再也接不到通了半天却无人言语的电话---父亲去世的第三天,母亲也撒手而去。父母一起相守了七十二年,冥冥中早已有了感应。父亲不忍抛下母亲,母亲生死守着父亲。父母用最美好的方式演绎了爱情的不离不弃,用最残忍的方式减少了一场葬礼的破费受累,用最决绝的方式警示了生活美好美好生活。雨已住,思不休;父母恩,永远在。[黄河原创文学]已经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运城网信备案L号
黄河原创文学推广团队
特邀顾问: 张高陵 申大局 王士敏 张开生
本刊主编: 姚普俊
图文编辑: 谭瑞平
小说审编: 谭锐金 郭 英
散文审编: 李亚玲
诗歌审编: 王秀娥
校园审编: 靳三涛
投稿邮箱:
qq.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wwjm.com/zcmbjc/111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