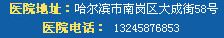各位看官,昨天一篇《南人北人,政商财商(二)》被系统删除,后台收到无数看官问候,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为了防止再度被删,或者被封号之虞,瞎猜思在此公布瞎猜思粉丝群 清脆的铃声和三轮车部件的摩擦声一起传来。6月19日下午3点,三轮车夫李子平终于揽到了一个活儿。拉着游客穿梭于距离北京天安门不足2米、面积为1.26平方公里、拥有条街道和胡同的大栅栏,是这位47岁的男子的谋生之计。
他一边努力蹬车,一边向车上的游客指点着周围,这是明清的建筑,这是民国的道路,那是解放后拉起的电线。
生活的压力让三轮车夫看上去更像57岁,尤其是粗糙的皮肤和斑驳的头发。他是地地道道的大栅栏“土著”,生在大栅栏附近,除了下乡外没有离开过这里。从年下岗之后的春、夏、秋三季,几乎每天吃完午饭,他就和他的三轮车出现在前门楼子。
车在胡同中穿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居民的住所--可以看得出,不少房子是主人自己搭建的--砖瓦的颜色青红杂乱。如果走进去,会是一种“三级跳”的感觉:路比院子高、院子比房间里高,最大的“落差”接近1.5米。
三轮车夫一家三口在两广大街附近拥有大约30平方米的两间平房。“这在大栅栏地区算是条件不错的。”他说。
随意的走访很快证实了他的说法:韩秀英,80岁左右,三井胡同居民。现居17平方米,一里一外的套间。小孙女出世以后,老人和儿子一家三口窝在这间屋子里。前年夏天儿子终于搬走的时候,孙女已经是22岁的大姑娘了。另一位已经退休的毕女士,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女儿以及外孙住在4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的是上下铺。
古老的胡同里几乎看不到空调的影子,每度0.4元的电费会让人心疼。电扇和火炉是大栅栏居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每年入冬,李子平都到附近的煤场,用他的三轮车拉回蜂窝煤取暖。
由于屋里没有上下水道,用过的水只能倒在房屋两侧,于是自然形成了两道水沟。很多人家无法在家中洗澡,距离炭儿胡同喻先生家数十米的地方有个公共浴池,洗一次澡十块钱,喻先生笑着说“十天八天去一回”。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厕——每天早晨,在胡同里的“旱厕”门前,都会排起长队。
尽管李子平拥有1.75米的身高、超过70公斤的体重,以及看起来很结实的肌肉,但“这是表面现象”。病痛缠绕着他的全身,在蹬车的时候,他甚至会停下来吃药。
他平均每个月收入大约元,但要负担上高二的女儿的学费。“所以我要拼命干活,明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不愿陌生人到家中造访,如同这里的其他居民,因为觉得是“贫得拿不上台面”。
在吃饭的时候能喝上廉价的二锅头白酒,是李子平最大的要求,尽管佐餐经常只有黄瓜、咸菜和一小碟花生米。而在韩秀英家,摆在黑白电视机旁边的晚饭也是西红柿打卤面。
“你知道一个月不吃肉是什么滋味吗?”这里的一位居民说。
“这就是北京穷人的生活。”李子平说,“昨天(6月18日)的报纸上登出来的,北京市社科院的调查报告,说这里一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8元,真真切切。”
在任何时候,矫情都要不得。眼光往上看,我们能发现自己的不足,眼光往下看,我们可能会庆幸自己的生活。
人生就是寻求一种平衡。就像走路一样。一旦你小脑萎缩,就容易失去这种平衡。很多人啊,我看就是小脑萎缩,如果再加上大脑发育不全,那就没办法了。
人啊,不能作,nozuonodie。人在做,天在看。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3
这两天在憋一篇大稿,值得期待。同时也是因为旅次途中,来不及细细整理思路。
昨天晚上,吃了一盘酱牛肉,想起《乾隆皇帝》里的一段故事:
乾隆和他大舅子傅恒的老婆偷情生的儿子福康安,在乾隆的一路栽培下,成了大清朝柱国,为乾隆到处打仗平乱灭火。在他从云南班师凯旋的路上,驻扎在洛阳,想吃洛阳当地有名的酱牛肉,就请了煮酱牛肉的师傅来自己的驻地宰牛煮肉,煮到一定火候,师傅对徒弟说,往大锅里放硝,徒弟说,忘带了。
师傅说:你上锅台,解开裤子,撒尿
尿里有硝。
小说里写,福康安尝了酱牛肉,觉得确实好吃,很鲜嫩。重重地赏赐了酱牛肉师徒。
发一篇去年的旧稿,是关于阅读《乾隆皇帝》的札记。
昨天早上,读了巫昂写的一篇文章,《这三十年里,中国小说的灵堂里供着的还有什么新鲜面孔》。
我认真想了想,最近几年,我读过的小说,好的,让我印象深刻,不能忘怀的,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再就是金宇澄的《繁花》。别的,好像没有了。
这两年,读的最多的,是高阳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抱着kindle,随便读一段,都能读下去。
《繁花》写尽了人生的悲凉。比如那一段:
蓓蒂变鱼后,姝华去吉林务农,给沪生写绝交信:“人已经相隔千里,燕衔不去,雁飞不到,愁满天涯…我们不必再联系了,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我就写到这里,此信不必回了。”
李静睿写过一篇《金宇澄的繁花开尽》,网上可以找到,值得一看。
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把清朝康乾盛世写出来,历史小说,写到这个份上,就我的阅读经验,无出其右。
作为三部曲的第一部,《康熙大帝》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顺治十八年正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刚过完年,一群一群的叫花子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又开始沿街乞讨。北京城哈德门以西的店铺屋檐下、破庙里挤满了这些人。一家家、一窝窝在城墙根搭起了破庵子、茅草棚,竟有长住下来的意思。好在自李闯王兵败以后,北京城内屡遭兵乱,人口十去五六。东直门内外瓦砾遍地,有的是空闲地方,不然真要人满为患了。这些人大都操关东口音,也有不少像是直隶、山东、河南一带的人,披着褴褛的袄子,腰间勒根草绳,端着破碗向人们讨饭。
“大爷大娘,积德行善,赏一口剩饭吧。俺是从热河逃难来的,上有老,下有小,没法子呀!”
“阿弥陀佛!罪过哟!大冬天的哪来的灾,跑这么远的路?”
一个肩头挑着补锅家伙的壮年汉子听了这话,将脸一扭停住了脚,冷笑道:“你是天子脚下的人,怎么知道乡下的事!他妈的,镶黄旗圈了老子的地,不要饭,吃毛?”说着把辫子往脖子上一盘,气哼哼地走了。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乾隆皇帝》的结尾,让人回味悠远。乾隆承诺了要把位子给嘉庆,却口惠而实不至,始终不愿意交出皇帝的印玺。刘罗锅去劝太上皇,终于说动了乾隆,答应把印交出来。
然后二月河写到:
刘墉慢慢退出来,殿外的风卷着小雪扑面一激,冻得他一哆嗦,才意识到天已黑了定了,几时进来,几时太监掌灯,竟全然没有在意……他身上带着殿中的余温,小雪花黑地里飘在脸上,倒觉适意的。悠着步子出隆宗门、到西华门外上轿,走了一程,觉得轿中还没有外头舒展,才想到是坐了一天费心费神费口舌的缘由。又觉饥上来,因在正阳门西下轿,吩咐:“你们先回去,我带小奚奴步行回去——把屋里弄暖和点!”因只带了两个小总角奴才跟着闲逛。
……已是年关近弥了,此时又是入夜,又飘着雪,空寥的正阳门前原本这时正是热闹不堪的夜市,但此时几乎不见行人影儿。因为地下盖了一层薄雪,雪光映着,隐约可见巍峨高矗的正阳门轮廓,和守城兵士旁星星点点的西瓜灯在风雪中晃荡。只有旁边关帝庙的寓舍里还住着人,那都是羁留京师的外地商贾和等待来年春闱的各省寓京举人住的,还闪着一扇扇门户的灯亮。也有几家馄饨烧卖小吃、汤饼摊儿、和烧鸡卤肉之类的担子摊儿,是专趁侍候这里客人的,点着稀稀落落的气死风灯,在砰、叭,零星的爆竹声间隙中凄凉叫卖: “馄饨——热的,一碗保您全身暖,两碗管教一身汗哪哎……” “烧鸡——瓜子儿!” “脆皮烧卖——正阳门刘家祖传高汤,一口一个鲜哎……”
……刘墉觉得饥上来,踽踽走近一个烧饼炉儿,用手煨着炉子问那卖烧饼的:“几个钱一个?”
“乾隆子儿俩一个!”卖烧饼的也是个小老头,摊子后头还有间小客屋,里头灯下影绰有人吃饭。听刘墉问,手里擀杖砰叭作响,搓着面剂儿头也不抬忙活,“里头有油茶,喝开水不要钱!”说着,掀开炉盖,在通红的炉膛里翻弄一下,又忙着赶剂儿。
“我来六个——我们三个人呢!”刘墉说道,回身把十几枚铜子儿隔案丢到钱匣子里。
那小老头看了一眼刘墉,伸着油光光的手从钱匣子里又如数把钱捡回来递给刘墉,笑道:“不敢收您的钱——是我积德!”
“为什么?”刘墉诧异道。
“小人认得您老。您是刘相爷。”小老头说道,“清官——茶馆里头整日说书;刘罗——”
刘墉一下子笑了,又把钱递回去:“就是罗锅子嘛——收下,你不收,我也就不是清官了。”
“成!我给您老多加点芝麻!”
小老头忙活着又用心做面剂儿,一面掀开通红的炉膛,不时地翻弄那溢着香味的烧饼。
隔二日后,乾隆与太子在太和殿授受玉玺成礼,嘉庆朝立。
大清帝国康乾盛世的浩荡风云,在买烧饼的小老头“我给您老多加点芝麻”声中收束,什么叫举重若轻,这就是。
牛逼的结尾,真不多见。
鉴于瞎猜思的读者客官多是苹果手机党,所以,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
谢谢您哪,我给您老多加点芝麻。
赞赏
人赞赏
长按中科白癜风医院用疗效说话北京哪个医院治白癜风好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wwjm.com/zcmbyy/68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