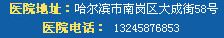龙应台写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们每个人,都是渐行渐远的"华安"......
今天为大家推送潍坊朗协副会长王远的文章《总有一份思念深埋心间》
总有一份思念深埋心间
作者:王远
春寒料峭,深夜失眠,至凌晨入睡。迷迷糊糊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去世十日的父亲,我想拉住他的手,他却越走越远.......慌乱中醒来,我已泪流满面。
父亲去世的头一天,我专程接来了父亲的老同学,已是年近八十岁相交六十年的单际田叔叔,两位老人双手相握彼此含泪无言。第二日下午,八十岁的父亲离去了。次日处理完后事,我向父亲的几位老友发了一个信息:家父已于三月二十日去世,后事今日处置完毕,疫情期间,未作即时告知。父亲的三位好友闻讯又特地赶来,老友诗人老丹带来了一幅挽联:新冠未除,一座杏林化鹤去;旧游谁约,三月桃花始盛开。老友魏修良长夜难眠,赋文追思《那片桃花还开着》;文友王健微博发文《有朋友,真好》。三月桃花始盛开,旧游谁约?每年的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父亲总是召集他的好友,开着他的小车,和他们一起赏花赋诗,开心的游玩于山水田间。如今,父亲去世后的日子,那片桃花还开着,我带着母亲去了那片赏花地,只是桃花依旧笑春风不见丛中赏花人。
坎坷大半生父亲总是笑谈人生,过往的乡亲朋友恩情牢记心间,也总是嘱托我们不要忘记;既往的屈辱与不公正的待遇少有提起,最困难的岁月里,父亲给我们定了《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再后来的《小说月报》,从小,我就是在书堆里长大。在那段父亲不愿意提起的岁月里,他内心一直在坚信,唯有知识改变命运。爱好文艺的父亲后来从医,一干五十余年,从医多年的父亲依旧有他难舍的文艺情结,时常写写文章,发发稿件,他的朋友,也都是当地文化名人,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贫苦的日子里,父亲纵使旧衣裹身,食不果腹,他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希望与自信,再苦难的岁月也保持着文人不向乱世低头的傲气与倔强,坚守风骨,儒雅温恭。陈平原教授在回忆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曾讲到: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气宇轩昂地屹立于天地之间。生长于田野阡陌间的父亲当然不能和老教授们相提并论,但是,我读到此文,我总是想起父亲的影子,这种不屈的精神和坚韧的灵魂,也深深的影响了我。
在外面谈笑风生的父亲回到家里,对孩子们却是沉默寡然又不拘言笑的。他的这种性情也在多年后让我和他有了距离,无论是求学在外,还是离乡工作数十年,从小我就养成了独自自主的性格,和父亲沟通的很少。回家的日子,我总是躲着他,不愿意和他有亲近的往来,我也看到父亲的眼中那份期待又不愿意张口,主动来和儿子坐坐聊天的眼神。母亲也尝试着我们爷俩还有姐姐、弟弟能和他走的更近一些,但每一次都无功而返。我曾走在家前面那条小路上,三十多年前,父亲在这里送我去读中学,从此,我离开了家求学在外。二十七年前,我考上大学,这是父亲那时候最高兴的事,开学的日子父亲坚持着一定要去学校送我,他把我送到了学校门口,遇到了迎接我已经早来的同学们,父亲默默的站在一边,又默默离开,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离去的背影是那么的孤单。
一直到我的外甥出生,父亲在外孙的面前终于丢掉了他严肃的面孔。我的儿子出生后,在高密家中住了半年多的时日,母亲告诉我,你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下班后推着他的孙子四处游转,至弟弟的孩子出生,大半生板着脸的父亲在三个孙子的面前彻底丢掉了他的严厉与沉默,成了孙子们的司机、厨师和保姆。也是在这些年,我与父亲的交流渐渐多了起来。十年前,我陪着父亲去了香港和澳门,在维多利亚海边,父亲第一次提出来要和我合个影,并破天荒的搂住了我的肩膀,这是我记忆中父亲和我唯一的合影。
慢慢的步入晚年的父亲也活出了他的精彩,享受他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九十年代初买了一辆摩托车,购置了两层楼的房子,买了当时最大的电视机,在六十五岁的时候居然去考出来驾驶证,据说是高密市年龄最大的学员了,教练员都叫他爷爷,父亲买了一辆微型雪佛兰,再后来弟弟给他换成了本田飞度,他在车后玻璃上贴了十六个字:白发老头,驾车新手,请多关照,平安共求。父亲开着他的小车时常与他的老友有花赏花,无花赏月,也开着他的小车来到潍坊我的家里看望他的孙子,拉着母亲去胶州看望老朋友,去水库边看草长莺飞。不服老的父亲又瞅上了奔驰斯玛特,一打听价格,又不舍得更换了。开了几年车的父亲越跑越远,母亲也总是不放心的跟着他,一直到从车库倒车的时候撞了墙上,父亲才恋恋不舍的放弃了他开车漫游的日子。我的堂哥给父亲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他已经是不能驾驭,后来,到我的儿子回家,十岁的儿子开着他的三轮车拉着他八岁的弟弟在门前道路上跑来跑去,他高兴之余又叹了口气:我这是上年纪喽!
父亲不开车的日子我回家总是拉着他出去转转,也时常的去看望他的老友。姐姐在工作之余,也领着他跑遍了大江南北,还去过朝鲜。父亲一直想去一次西藏,因为年龄的原因我劝阻了他,后来也想去一次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逃难去的甘肃平罗,是在前年,姐姐带着他跑到了山西,因为身体的原因又折返回来。年的父亲因为兵乱避难青岛崂山的烟云涧村,六十二年后,我多方联系查找,领着他和伯父来到了这个海边山村,站在海边礁石上的父亲感慨万千,我抓拍下来了这张照片,回家后也为他写诗一首:儿时避难烟云涧,回首六十二年前,沧桑半生风雨路,都付笑谈烟云间。父亲非常的喜欢这幅照片,放大后并请他的老友王钦安题字,一直摆在他的卧室里。父亲还想着去一次台湾,我的爷爷在年随国民党军去了海峡彼岸,已经在年去世,他想着和伯父去台湾走走看看,那里或许能找寻到我爷爷生活的痕迹,但颇多原因没有成行。年,我来到了台湾,在一个雨夜找到了爷爷医院,经多方探询,获知放置爷爷骨灰的那个宝塔在年的一次洪水中被冲的踪迹皆无。台湾归来,我告诉父亲爷爷的事情,他豁达的说到:既然已经冲到大海里,或许他早已经魂归故里。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因为小脑萎缩,已经不能走动和进食,也丧失了语言功能,我赶回家中,五天的时间我与他朝夕相伴,父子执手依旧是相对无言,父亲忧伤的眼中留下浑浊的眼泪。父亲去世了,没有太多的痛苦,那一天,我也没有太多的悲伤,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活着的时候做好晚辈该做的事情,走的时候也就安静的离开,虽有诸多的不舍,可又是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呢。处理完父亲的后事,陪伴了母亲几天,我回到潍坊的家,疲惫无语的坐在沙发上,幼小的儿子走过来问:爷爷呢?我的眼泪立即涌上眼眶,我告诉儿子:爷爷离开了,你的爸爸再也没有爸爸了。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但是总有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然后走过来,陪我一起。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火,然后快步走过去,生怕慢一点他就会被淹没在岁月的尘埃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
如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言: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作者王远:潍坊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潍坊米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欢迎转发分享~其他公众平台转载,请注明出处!投稿发送邮箱:wf_langsong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wwjm.com/zcmbyy/121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