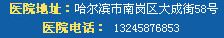编者按
清明节这天,一场春雨如期而至,纷纷淋淋地飘洒向大地,从早到晚,断断续续下了一整天。满眼望去,料峭春寒中的新绿,如烟如诗。侧耳静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如泣如诉。乍暖还寒,胜景哀情。
年是英华人最为伤感的一年。李观仪先生和杨小石先生,一个在年初,一个在岁末,先后离我们而去。清明时节,我们更为想念两位先生。
这里发表李尚宏、孙会军老师的纪念文章,以表达我们的思念之情。——李先生、杨先生,您们在天堂都好吧?
为师当如李先生
——怀念李观仪教授
李尚宏
年2月6日,我正在和家人外出度假。整个上午,心里都莫名地不安,有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中午时分,先后接到明建院长和李先生亲属的消息,告诉我李先生清晨逝世的噩耗。
对李先生来说,这未免不是解脱——毕竟她已经卧床多年,身体非常虚弱,时刻离不开氧气。近一、两年来,她对生命越来越悲观;我探望她时,她总是一再重复“早点跑路”。李先生去世时几乎没有痛苦,非常安详,这是她的福气。
然而无论如何,我心里总是非常悲伤。想到再也不能见到慈祥的李先生,再也不能和她亲切交谈时,鼻尖一阵阵酸楚。
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是在年秋天。入学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三号楼门厅的书店旁,看到一个衣着非常朴素的老太太坐在一把椅子上专心看书。我心里想,大学到底是大学,连清洁工都这么用功读书。后来,我知道那个读书的“清洁工”正是我们精读课本的主编、大名鼎鼎的李观仪教授。当时李先生还没有退休,还在编写《新编英语教程》5-8册,并且给研究生上课。我碰到她的那天下午,她正好在门厅等待学校专门派来接送她上下班的小车。我责怪自己有眼不识泰山。然而李先生的装束实在朴素得令人惊讶:一身发白的蓝色涤卡布中山装,两个最简单的布袋,一个装书,一个装饭盒。熟悉李先生的人都知道,一直到老,这身蓝涤卡中山装是李先生唯一的正装。
李观仪教授上课照片
年,我毕业留校工作,算是和李先生做了同事,但接触很少,一般都是在走廊碰到后,毕恭毕敬地说声“李先生好!”李先生对我也未必有印象。直到年,我才有机会和李先生有了实质性的接触。那年李先生的干部医疗证(红卡)需要更换。我当时在学校组织部,正好负责这项工作。李先生的证件已经过期,换证比较麻烦。我就一手包揽了跑腿的事情。大概是因为我服务比较殷勤,李先生记住了“组织部的那个小年青”。
真正和李先生交往是从年开始的。当时,我正在编写教材《英语阅读与学习技巧》(上、下册),李先生亲自审订了两本教材,帮了我大忙。这套教材的油印版在英语学院已经使用了三、四年,我对质量还比较自信;让李先生审订,本来也只是想让她挂个名。那年夏天,我到她家,冒昧地提出想法,没想到她一口答应。在近三个月的审定过程中,我领教了李先生的治学的严谨。我原本还比较有把握的两本书稿被李先生批改得每页都密密麻麻。每次面谈,她往往会指着某处的英语表达,质问我:“这算什么东西?”上海的夏天闷热,李先生家又没有空调,本来就爱出汗的我在李先生接二连三的质问下总是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乱了阵脚以后,我细心琢磨编写教材的学问。而李先生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自然就是我学习的最好范本。因为曾经学习过,我一度认为熟悉这套教材。然而当我从编者的角度学习时,才发现《新编英语教程》选材经典、考究,练习设计精巧、到位,就连每一处的注释都非常准确;整个教材严谨细致、英语表达地道,几乎无懈可击,的确是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在李先生的大力指导下,我对两本教材几乎全部返工,教材质量当然全面提升。然而,欣喜的同时,我内心对李先生的感激也与日俱增。李先生当时虽然身体还好,但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为我如此付出,让我既感动又愧疚。教材出版后,我打算把第一次稿费(元)全部给李先生,以表示感谢。当我把信封递给她时,她非常不客气地拒绝了,并说再提钱的事就赶我出去,吓得我只好打住。我也多次带着精美的礼品、食品去看李先生夫妇,但每一次都被他们拒绝,不仅如此,还往往带回亲戚朋友送给二老的礼物。
李观仪教授就教材修订内容与国外学者探讨交流
一来二去,我成了李先生家里的常客。年以后,我回到英语学院工作,有更多机会接触李先生,有时帮两位老人办事,但大部分时间是聊天。起初还电话约时间,后来他们就让我随时直接上门了。每次见面,我叫她“李先生”,她说:“你也是李先生,只不过年纪是我的一半”。渐渐地,我们谈得越来越多,笑声越来越频繁。很多人都觉得李先生严肃,甚至不苟言笑,我却觉得李先生非常平和,言谈中不时地冒出她特有的幽默。往往谈兴正浓,李先生夫妇就留我吃饭。饭菜虽然简单,李先生却非常讲究时令、搭配,等等。经过我多次发动,年春天,他们同意跟我外出走走,一次去外面吃饭,一次去了南汇的滴水湖和鲜花港。那时候,杨先生因为小脑萎缩行动不便,李先生行动基本自如。两位老人长期在家,偶尔外出兴致很高,也让我很欣慰。
有较长一段时间,我在学校是有名的“王老五”。李先生和老伴都很关心,还张罗给我介绍过对象。虽然没成,但两位老人亲自出面为我牵线,着实令人感动。年,我终于结婚了。李先生和杨先生非常高兴,亲自参加了我们小规模的结婚典礼。两位老人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他们的光临让只有五桌的酒席的规格提高了许多。我结婚后,邀请两位老人到我家做客,他们欣然接受。我和妻子厨艺一般,但两位老人很高兴到我家看看。再后来,我经常带着儿子去看望李先生。她特别喜欢小孩,每次都给我儿子许多食品、礼物。我儿子也特别喜欢“那个病房里的奶奶”。
年春节后,我刚从老家回来,就从冯庆华副校长那里得知李先生生病了。原来,冯校长和徐秋园老师春节前去看望李先生时,发现她腰疼。冯校长立即叫了救护车,送李先生住院。李先生的身体本来很好,但因为缺钙,导致严重的骨质疏松,脊柱压迫性骨折。李先生曾一直骄傲地说自己年轻时一米六八。但从这以后,她越来越矮,原因就是脊柱变形。这本来并不严重,但可怕的是脊柱压缩、弯曲以后压迫了肺,限制了肺的扩张,导致缺氧。李先生其它身体器官都很好,健康指标都正常,只有这个病在晚年一直困扰着她,并且越来越严重。
年,李观仪教授在重阳节与退休教师聚会
医院的干部病房,虽然请了护工,但医院隔三差五地就叫家属。李先生没有子女,老伴也行动不便,于是我就担当起了家属的角色。李先生享受干部保健,医药费全部报销。医院经常因此总是要做一些并不是必须的检查:核磁共振、脑CT、肺CT、心脏彩超,等等,而且每次都要家属到场。于是我就经常推医院的各个辅助科室。医院里的人都以为我就是她的儿子。开始的时候,我还解释一下,时间长了,我也随他们去叫了。倒是李先生听着很高兴,每次都笑得合不拢嘴。
人老了总是有些怪脾气。李先生每次住院前总是很不情愿,怎么都觉得家里好。我只好三番五次地又哄又劝。住上一段时间以后,医院因为周转病床的需要,让她出院,医院条件好,不情愿回家。我又只好五次三番的又劝又哄。刚住进去的时候,李先生往往因为心情不好对医务人员少言寡语、不苟言笑,引起他们的误会。我知道以后,赶紧给护士站送花,给他们介绍了李先生的背景和她在师生中的口碑。在这之后,医务人员对李先生的态度明显好转。
住院时间长了,李先生难免感到孤独。我给她买了手机,她也学会了使用,经常和家人、亲戚、朋友通话。在同事中,她尤其喜欢和李佩莹、江则玖等老师聊天。在英语学院的大会上,我经常向全体老师通报李先生的情况。除学校领导、职能部门、学院领导班子和工会等组织以外,李佩莹、江泽玖、何兆熊、章伟良、徐文文、蓝茹、贺云、龚芬、张艳莉、徐秋园、董严泓等多位老师都非常关心李先生的健康情况,多次主动探望李先生。为了帮李先生解闷,医院工作,我们尽量分批前往。这样一来,李先生每次住院,总有同事、学生隔三差五地前去探望。不仅病友羡慕,医务人员也对李先生刮目相看。每次有人来,李先生总是特别开心,她非常喜欢和老朋友、晚辈们聊天,而礼物照例一律不收。这也让前去探望的人很困惑。很多人提前私下问我李先生到底喜欢什么。经过长期观察,我发现李先生早餐喜欢吃全麦面包和酸奶。然而,送这两样的人多了,李先生又坚决让人家带回去。
年,李观仪教授与学院青年教师合影
李先生对教育事业、对上外感情深厚,长期从事公益捐款。据我所知,他们通过“九三学社”等多个组织向上外贫困学生、西部学生、上海某些中学多次捐款。年,李先生夫妇跟我商量,要把他们大部分积蓄(起初计划万,事实总数万)捐赠给学校。李先生的原话是“这些钱取之上外,用之上外”(她觉得稿费是上外给她的)。在给学校的信中,她说他们夫妇没有培养子女开销,也没有烟酒之累,所以将多年积蓄捐给学校,委托我全程办理。我非常清楚,李先生夫妇除工资和稿费以外,并没有其它收入,也从不理财,一百多万的确是他们大部分积蓄,其中主要是李先生编写教材稿费所得。学校领导得知后,害怕捐款影响两位老人养老,多次让我劝说他们不要捐,或者以后再捐。但李先生夫妇非常坚决。学校领导希望通过李先生的善举教育学生,但李先生坚持不公开、不留真名,并说:“要公开我就不捐了。”最后,经过再三商量,两位老人同意用假名捐款,奖学金取名“林芯奖学金”(“林”是从李先生和杨先生的姓中各取一个偏旁,“芯”意即一片寸草心)。那年夏天,我前后去了十几次银行,把两位老人不同数额、不同日期到期的定期存款取出并存入学校账户。这些钱都不是整数,明显是李先生的稿费。每次取款,我都被深深地感动。
年,李观仪教授与丈夫杨德顺先生在松江校区合影
李先生夫妇生活极其俭朴,吃穿用度,都省得不能再省,这并不是他们没见过世面、不知道奢侈、或者不会花钱的结果。在多次交谈中,我了解到,李先生出生在富裕的书香门第。父亲是中国银行(民国时期的央行)的高级职员(李先生在档案中只写“职员”,大概是为了避免极左时期的审查),家里有七、八个佣人,有汽车、专职司机,住“模范村”两个单元的房子。李先生年幼时先后到北京、香港上学,就是因为父亲职务调到的原因。李先生曾骄傲地说,他们兄弟姐妹六人,全都上圣约翰大学。圣约翰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很难考,学费也高昂。李先生一家仅父亲工作,供养六个子女就读圣约翰,后来还资助李先生去斯坦福大学留学,家庭经济可见一斑。李先生真正经济拮据是在美国留学期间。年开始,在没有家庭资助的情况下,她勤工俭学,在斯坦福食堂打过工,也为当地人家做过专门烧饭的保姆(这真有意思,一个从没下过厨房的中国大小姐,到了美国能给人家做厨师。不知道李先生当时的雇主怎样评价她的厨艺)。毕业以后,她有机会留在美国工作(美国当时给几乎所有在美中国人美国公民身份),此外,当时对新中国谣言四起。李先生说:“我当时就是不相信他们共产共妻,一定要回去看看”。这样,她放弃了留在美国的机会,回到物资匮乏的新中国。主编教材成功以后,李先生在很多人眼里是“有钱人”。但很少人知道,李先生的稿费不算多,而且她对钱从来不闻不问。老伴在世时,家里的经济是老伴管。老伴去世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由他的外甥负责。有亲戚让李先生“心里有个数”。李先生对我说,“有吃有穿,要钱干什么,随它去吧”。
年7月,李先生又一次住院,一直到去世,医院的干部病房。由于杨先生在去世前委托外甥沈汉侯先生全权照顾李先生,也由于我长时间出国访学,医院的时间比以前少了许多。每次我看她,她都问起学校、学院的许多同事,也必然问候我家里的每一个人。每次别人去看她,她也一定提起我。据说在她生命最后阶段,她感到非常孤独,也常常念起我。而我耽于杂事,没有多去陪陪李先生,真是遗憾之至。
年,英语学院领导及老教师们为李观仪教授九十华诞祝寿
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李先生让人肃然起敬。这恐怕是因为李先生做到了我们向往但无法达到的人生境界:生长于富贵之家却一生弃绝浮华,置身喧嚣都市却始终恪守生命本真,经历百般世事却向来从容淡定,勤奋工作却只求有功于社会,成就卓著却从不恃才傲物……人生不过百年。而李先生的人生活得本真,活得精彩,活得让人发自内心地敬仰。
我是非常幸运的,在李先生的晚年,我有幸成为从没有进过她课堂却获益最多的学生、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朋友。
往事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一个大学,最重要的是传统。李先生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元老之一,为后辈树立了最有号召力的榜样。她的人格、她的作风都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并发扬的传统。
李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我永远是李先生的学生。
我们的翻译大家杨小石先生
孙会军
又到了芳草萋萋、细雨霏霏的清明时节,心情也随着阴郁起来。去年刚刚离我们而去的李观仪先生、杨小石先生,再次引起大家的唏嘘感叹。天堂里的他们一切都好吧。
我没有见到过李先生本人,但杨教授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去年九九重阳节,学院为章振邦教授、杨小石教授祝寿,章先生没有亲自过来,杨小石教授当时虽然已经95岁高龄,但是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一个人来参加活动。当时担心杨先生年纪大了,我提前一天电话到他家里,问他要不要我们去家里接他,他谢绝了我们去接他的Offer,第二天一大早,一个人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一般瞬间来到英院,真是让我们大家既震撼、又欣喜。跟我们大家团聚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耳聪目明、博闻强记、思维敏捷、知识渊博。
杨小石先生是西语系、乃至英语系的创始人,他从头到尾见证了英语专业从西语系、到英语系、再到英语学院的发展历程。杨小石先生一生译著等身,译术高超,留下了很多经典译作,成为英语学院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对于我们这些新的英院人来说,杨小石先生无疑是上外英院不老的神话。了解杨小石教授的翻译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了解英院的历史。我当时因为带了几个本科生申报了一个创新项目“杨小石教授的翻译思想与实践的”,因此带着学生在学院跟杨教授座谈了一次,还有一次跟徐文文夫妇到他家里拜访。因为接触有限,相对杨教授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了解到的最多也就是一鳞半爪,但是我们感觉已经学到了很多。
杨小石先生年出生于北京一个中西合璧、家学渊源的书香门第,从小在中西文化的浸润下长大。母亲杨燕妮是瑞士人,父亲杨仲子曾旅居法国、瑞士十六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北京艺术学院,并担任文理学院的系主任和北京艺术学院的院长,是我国最早从事西洋音乐传播的教育家、音乐家。他小学读的是法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中学转入美国人开办育英中学,表现出突出的英语、法语天赋,深得美国校长的喜爱。中学就读期间,除了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还得到美籍校长定期额外的指导,阅读了大量文学经典,为后来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杨小石先生考入复旦大学外语系,受教于梁宗岱教授、全增嘏教授、林同济教授、洪深教授、徐宗伯教授和杨宪益教授。其中,洪深教授和杨宪益教授对于他走上翻译道路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洪深是著名戏剧家,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解放后调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副局长期间,专门在上海设立了一个翻译点,请上海各大学的老师承担对外文化事务联络局的一些翻译任务,而审阅汉译英稿件的任务就委托给全增嘏教授和杨小石先生。以英译《红楼梦》而著称的译者杨宪益先生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复旦读书期间,他选过杨先生的课,因为杨宪益曾经到复旦兼课。除此之外,他跟杨宪益先生还有更近一层关系。当时杨宪益在重庆北?的国立编译馆工作,他父亲杨仲子先生辞去公立音乐学院担任院长的职位后,到国立礼乐馆工作,而国立礼乐馆和国立编译馆很近,两家人就在重庆北?的同一栋楼里比邻而居。读杨宪益先生的传记了解到,那栋楼后来以“三杨楼”而著称。所谓的“三杨”,指的就是杨先生的父亲——音乐家、教育家杨仲子教授、从事国乐教育的杨荫浏教授和从事翻译工作的杨宪益教授。杨宪益在他的《零墨续笺》的序言中提到,他在国立编译馆以英语翻译《资治通鉴》的时候,经常与杨仲子等学者讨论、交流,获益良多,由此看出两家人之间交往很深。因为有这样的机缘,杨小石先生经常有机会接触杨宪益、戴乃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杨宪益先生出任ChineseLiterature的主编,因为对他的外语能力很了解,经常请他承担翻译任务,为他发挥和展示自己的翻译水平提供了一个平台。
杨小石教授与同事们在一起
杨小石先生是上外西语系以及后来英语系的奠基人和顶梁柱,曾经从事修辞学研究,在外语教学方面也很有建树。他除了在学校承担教学任务之外,还主持过各类英语教学广播节目,在全国的英语教学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和爱荷华大学访学期间,讲授过“电影史”这门课,颇受美国学生的欢迎。这无疑得益于他渊博的知识、风趣的表达和地道的英文,但是我们觉得跟他多年来丰富的翻译实践,尤其是影片译制实践不无关系。
杨小石教授在从事翻译工作
杨小石先生在翻译上花去了很多时间。他的翻译,既有英译汉,也有汉译英。英译汉作品都是著名作家的经典名作,其中包括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长篇小说KingsbloodRoyal(《王孙梦》)(中文版年出版)、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DrySeptember(《干旱的九月》)和《他的寡妇的丈夫》(收入一部独幕剧的译文集)等。
杨先生的汉译英做得更多,经常在杨宪益主编的ChineseLiterature上发表译作,我们最近找到了杨先生五十年代发表在ChineseLiterature上几篇译作:
1.周扬的《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2ChouYang-TheReformandDevelopmentofChineseOpera
2.蒙古族作家朋斯克的《金色兴安岭》.4Punsek-TheGoldenKhinganMountains
3.沙汀短篇小说两则.2TwoShortStoriesbyShaTing——《磁力》(TheMagnet)和《一个秋天晚上》(AnAutumnNight)。沙汀的这两部短篇小说的译文,杨先生在美国讲学的时候,无意在penguinbook丛书中看到过,译者署名的地方,写的不是杨小石,而是ShangWaiying,也就是上外英语专业。原因呢,我们猜测,主要是发表在ChineseLiterature上的译文,译者是不署名的,企鹅丛书的编辑估计听说译者是上外英语系的老师,所以给译作贴上了“上外英”的标签。
上面的这两个短篇,虽然没有署名,但毕竟还是出版了,而且还是第二次出版,其实杨先生还有一些作品花费了很多心血,却最终没有能够出版。他翻译过法国作家罗杰·瓦杨的的两部小说,一部是《三十二万五千法郎》,另一部是《波·马斯克》,前者是受上海译文出版社之托而译,而后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的,因为作者受到斯大林的推崇,所以两家出版社都急于将他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但是后来中苏两国的交恶,这两部作品最终都不了了之了。还有一部译作的是电影版莎剧MuchAdoAboutNothing。杨先生受上海电影译制厂委托,翻译了这部电影。剧本他翻译好了,电影配音也做好了,但是后来却没有公映。另外一个无疾而终的是他花费四年时间完成的一部原创英文小说HazardsOftheunknown《未知的风险》,看到当时发生的老舍等文化名人的悲惨结局,为了不给自己找麻烦,最后狠狠心将这部四百多页的作品付之一炬。
杨先生着力最多的是中国电影的翻译和配音。他跟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制片厂和上海科技制片厂密切合作,先后把近百部国产影片翻译成英文,并为这些电影配制了录音。他翻译的电影涉及科技、教育、美术,故事片,大小长短不一,各种题材和体裁都有涉及。他最早翻译的是《聂耳》,后来搞了一个比较重磅的东西就是《舞台姐妹》(年上映),那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片子,英文配音的《舞台姐妹》后来曾经拿到中美飞机航线上播放。他翻译的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影片,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至今还留存着对这些影片的记忆。
《大闹天宫》(英文定稿)(年动画电影上映)
《大庆战歌》(年上映)
《闪闪的红星》(年上映)
《小花》(年上映)
《哪吒闹海》(年上映)
《春苗》
《梅花巾》(年上映)
《沙鸥》(年上映)
《崂山道士》(年上映)
《孔雀公主》(年上映)
《候补队员》(年上映)
《武当》(年上映)
《特区姑娘》(年上映)
《大漠紫禁令》(年上映)
《人鬼情》(年上映)
《熊猫学木匠》(动画片)
《小毛孩夺宝奇缘》(年上映)
《大足石刻》(年央视纪录片)
杨小石教授参与翻译的部分电影作品
此外,杨先生还翻译过几部昆曲唱辞,如《牡丹亭》、《人逢今世缘》等。他的翻译完全押韵,一行对一行,这个难度非常大,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文学性表达的再现效果非常好。杨先生翻译的两三部动画片也是押韵的。
杨先生最重要的业绩和成果都是在-80年代,时间有点久远,现在的学生和读者都不太知晓。查明建院长就建议我带领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好好搜集、整理下杨先生翻译的各种译作,并加以研究,阐发杨先生翻译事业的价值、意义。杨先生的译作,不仅仅是重要的史料文献,还凝结着杨先生的心血和才华,是不可多得的翻译教材和珍贵的翻译学习资料。认真学习和比对杨先生的翻译,无论对我们的翻译教学的改进还是对我们翻译能力的提高都大有裨益。搜集整理杨先生的这些译作,还有助于找到“中国电影”、“中国文学”乃至中国走出去的有效途径。杨先生所翻译的近百部电影都是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我们在对外宣传方面的积极尝试,对于我们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杨小石教授部分代表作
因我带领学生整理、研究杨先生的翻译成就,因此去年学院举行的重阳节座谈会,查老师就安排我代表学院做一个发言,宣讲杨先生杰出的翻译成就,向杨先生祝寿,表达后辈的敬意。记得我当时说,九九重阳,九与长久的“久”同音,包含有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寓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希望杨先生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继续为英院这个大家庭的繁荣发展尽心尽力,没想到重阳节过后两个星期,杨教授突然身感不适,老干部处医院,查老师、孙老师闻讯也连忙赶去。医院不久,就与世长辞了。
年英语学院重阳节活动合影
很多人都感到很意外,大家都在想着给杨教授过百岁生日呢。还清晰地记得他在电话里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如何痴迷于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他是孙俪的粉丝;还记得他谈起他对于当前电影翻译的困惑,为什么字幕翻译就这样取代了电影配音,当年他自己为了对口型花了多少精力啊;还记得重阳节杨教授跟我们告别的情形,当时他走得非常匆忙,赶到老干办去参加另外一场活动,还记得他骑着摩托车远去的背影。半个月后,他匆匆离去,一直留下一个错觉,感觉得他骑着摩托车走了,去追求让他痴迷的各种美好。
借清风一缕,捎去我们的祝福,惟愿老师安好。
文案┃李尚宏、孙会军
编辑┃查明建、宋亮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wwjm.com/zcmbwh/11535.html